派阀解散,日本政坛生态的深刻嬗变

2024年11月11日,日本首相石破茂(前排中左)准备在日本东京的首相官邸率阁僚合影
文/项昊宇
编辑/吴美娜
7月份举行的日本参议院选举,可视为日本政坛阶段性变化的一个结果。而在此之前,6月25日自民党派阀“官宣解散”,从更深维度昭示了日本政坛的一种重要转变。
当天,执政党自民党内的最大派阀“安倍派”(清和政策研究会)向总务省提交解散备案,为其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生命画上了句号。至此,因“黑金”丑闻而备受攻击的自民党五大派阀(“安倍派”“森山派”“岸田派”“茂木派”“二阶派”)已悉数解散。“安倍派”正式解散后,自民党内仅剩下前首相麻生太郎领导的“麻生派”一个派阀。
这场由政治资金丑闻引发的巨大震荡,似乎以一种决绝的方式,宣告了日本“派阀政治”的终结。然而,在旧的权力结构轰然倒塌之时,一场新的权力重构已悄然拉开帷幕。日本政治真的迎来了“换新衣”的深刻变革,还是上演一场精心编排、意在转移视线的“政治秀”?在新的内外形势下,日本政治生态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嬗变。
竞逐权力巅峰——派阀政治的前世今生
自民党的派阀政治是日本政党政治的核心特征,深度嵌入日本权力政治的运行体系之中。派阀的诞生可追溯至1955年的“保守合流”。当时,为组建自民党,背景不同、利益各异的保守派政治势力聚集一堂,这些原生的小团体便是派阀的雏形。它们并非基于现代政党理念,而是延续了战前政治家个人门生、地缘、官僚背景等形成的人脉组织。
在战后自民党长期执政过程中,各派阀自成一体,逐渐形成以领袖为核心,通过集体行动来争取资金分配和职位安排的利益共同体。派阀既是培养政治人才的摇篮,也是角逐党总裁宝座(即首相之位)的权力来源。
尽管自民党各派阀政治倾向和政策主张不同,但较之于政策竞争,彼此关系更多表现为对权力的争夺。派阀运行方式可总结为“金钱与职位”的分配。派阀领袖通过为成员提供选举资金和日常活动经费,并在内阁改组和党内人事安排中通过为其争取大臣、副大臣等关键职位,来换取成员在总裁选举中的选票和绝对忠诚。这一机制使得派阀成为角逐首相宝座的“选举机器”和培养未来领袖的“预备学校”。
长期以来,自民党内各大派阀力量的此消彼长,主导了战后日本政治的演变轨迹。20世纪60年代,在奉行“重经济、轻军事”的“吉田主义”路线下,“宏池会”如日中天,与开创了“金权政治”的田中角荣所领导的“经世会”展开激烈竞争,首相辈出。
进入21世纪,在日本政治右倾化背景下,“清和会”长期主导日本政坛。与此同时,自民党派阀政治的衰落进程不断加速。日本民众对“金权政治”的厌恶、选举制度改革对派阀集票能力的削弱等,都持续侵蚀着其根基。2023年末爆发的“政治资金派对回扣丑闻”,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一丑闻系统性地暴露了派阀利用法律漏洞建立秘密资金库的腐败本质,引发剧烈的政治地震和民意海啸。
时任首相岸田文雄以壮士断腕的姿态推动派阀解散,意在回应汹涌的民意,挽救自民党岌岌可危的声望。自2024年初起,除麻生派外,安倍派、岸田派、二阶派、茂木派等主要派阀相继宣布解散。然而,正如日本著名媒体人鲛岛浩所指出的,“只要有自民党总裁选举,派阀决不会消失”。这句论断一针见血指出了问题的核心:只要权力的分配逻辑不变,政客们合纵连横、抱团取暖的动机就不会消失。

2024 年 9 月 27 日,自民党总裁候选人高市早苗(右一)在日本东京自民党总部进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投票
派阀解散——一场切割止损的政治决断
“政治资金派对回扣丑闻”的核心是,自民党内多个派阀为所属议员下达超出配额的政治筹款派对券销售任务,超出部分的收入以“回扣”形式返还给议员,且这部分资金大多未被记入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从而形成秘密的“小金库”。这一操作手法精准利用了日本《政治资金规正法》的漏洞。该法规定,对于购买超过20万日元派对券的个人或团体,必须公开其身份。
为了规避审查,大额献金常常被拆分成多个小额,或者干脆就不入账。派阀将超出销售指标的资金返还给议员,实质上构筑了一条隐秘的利益输送渠道。这些不透明的资金,成了议员们在选区内进行婚丧嫁娶、迎来送往等“关系维护”活动的本钱,也是派阀领袖用以笼络人心、控制成员的“胡萝卜”。
面对媒体的穷追猛打和民众支持率的断崖式下跌,自民党看似雷厉风行的解散行动,与其说是刮骨疗毒的自我革命,不如说是一场精心计算的政治止损。通过将问题归咎于“派阀”这一组织形式,自民党试图将系统性腐败淡化为特定组织结构的历史遗留问题。
然而,解散政治团体法人,仅仅意味着派阀不能再以官方名义筹集和分配资金,以及失去了固定的办公室和职员。但构成派阀核心的人际网络、忠诚关系以及共同的政治利益,并不会因此烟消云散。议员们仍然会通过聚餐、开会维系小团体联系,领袖们也仍会为“派系子弟”的选举和职位奔走。旧派阀的组织架构虽然解体,其精神内核和功能性需求依然存在。
日本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抨击道,这场看似彻底的“解散”,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次“障眼法”,是自民党为应对舆论危机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而非对“金权政治”本质的清算。
更重要的是,派阀解散并未改变自民党内权力生成的机制。只要自民党总裁依然是日本政治权力的顶峰,那么为了争夺这一职位而形成的政治团体,就必然会以各种形式“借尸还魂”。
自民党总裁选举是“国会议员票”与“党员票”的结合,前者占据更大权重。获得尽可能多的国会议员支持,是当选党总裁的必要条件。一个有志于问鼎首相之位的政客,需要一个忠诚的团队为其出谋划策、筹集资金、联络各方,并动员尽可能多的议员投票,而派阀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有效工具。派阀解散后,这种逻辑并未改变。
2024年9月27日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已宣布解散的岸田派、茂木派、二阶派、安倍派等虽然无法强制要求其成员采取统一行动,但第一轮投票依然表现出鲜明的派系倾向。只是由于缺乏众望所归的人选,各派未能实现有效的合纵连横,最终让“无派阀”的石破茂“捡漏”。
面对外界对于派阀解散“换汤不换药”的质疑,自民党提出的改革方向是将党内派系改造为纯粹的“政策集团”,剥离其筹款和人事分配功能。然而,现实的演变似乎正在验证外界的担忧。旧派阀的成员们并未完全散去,而是以更松散、更隐蔽的方式继续活动。旧安倍派的骨干成员、旧麻生派的核心人物以及旧茂木派的部分成员,依然定期举行会晤,延续着派阀时代的议事传统。
与此同时,新的政治团体也在浮现。这些新团体往往围绕特定的政策议题或依托强大的个人号召力而集结。以保守派立场闻名的前经济安保担当大臣高市早苗、“未来之星”小林鹰之等人瞄准未来的党总裁大位,正在集结支持其政治理念的议员,酝酿成立新的政策研究会。前首相麻生太郎则利用其仅存的官方派阀“麻生派”,继续发挥在党内政策上的影响力。
这些新老团体都刻意淡化了传统派阀的“金钱”色彩,转而强调“政策”和“理念”,但这只不过是在新的“政治正确”下的一种生存策略。只要争夺首相大位的权力政治逻辑不变,任何形式的团体都有可能演变为事实上的“新派阀”。

2019 年 4 月 12 日,在美国华盛顿,当时的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
未完的政治变革——“无派阀时代”的混乱与迷惘
自民党派阀的解散无疑对日本政治生态造成了巨大冲击,一个趋于碎片化、流动化和难以预测的政治生态逐渐形成。传统派阀的解体,首先冲击的是自民党内原有的权力制衡结构。过去,首相的权力受到党内各大派阀领袖的有力牵制。如今,随着各大派阀的“龙头”消失,议员们不再有明确的归属和效忠对象,自民党内部的权力结构呈现出“流动化”特征。
就现任首相石破茂而言,他成为“无派阀时代”的首个受益者。其在“黑金”丑闻冲击中当选党总裁,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他无派阀的“独狼”背景。在自民党处于颓势的大背景下,尽管石破茂支持率低迷,但由于主要竞争对手的派阀基础被瓦解,党内无人敢于公开“叫板”,使得他在党内的地位相对稳固。尽管缺乏强有力的党内根基,但因为失去了强大派阀的掣肘,石破反而可以相对自主地推动各项政策议程。
当然,这种权力基础是脆弱的。当议员们不再受派阀纪律约束,他们在国会投票和政策议题上的行动将变得更加难以预测。首相将不得不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与一个个独立的议员或小团体进行谈判和交易,执政成本和不确定性都大大增加。一个没有稳定支持基础的首相,其政权也必然是根基不稳。
派阀的解散,本身是日本政治在“黑金”丑闻重压下的一次应激反应,其解散彻底埋葬了“五十五年体制”以来主导日本政坛的旧有权力结构。但日本政治的沉疴仍在,金钱与政治的纠葛并未被彻底斩断,围绕总裁选举的权力斗争依旧是政治运作的核心。未来依托不同政策主张或个人号召力的新团体,能否真正取代派阀主导的权力格局,重塑自民党内的力量版图,依然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从大的时代背景看,自民党的政治变革,也是顺应自媒体、新媒体时代的一个必然选择。目前自民党和公明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已经失去众议院过半数议席,正面临2009年以来最大的执政危机。如果自民党不能真正“改头换面”,旧的利益共同体在“政策集团”的伪装下得以重生,“权力游戏”故态复萌,也可能会再度被民众抛弃,迎来第三度下野的结局。而这场未完成的政治革新,正在将日本政治带入一个充满变数的迷惘路口。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本文截稿时间为2025年7月18日18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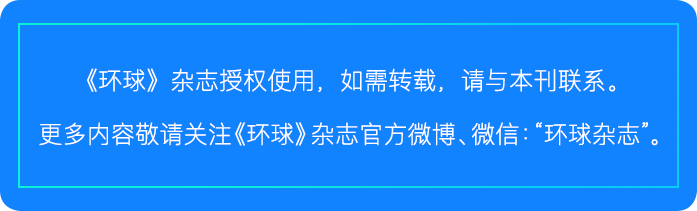

 手机版
手机版